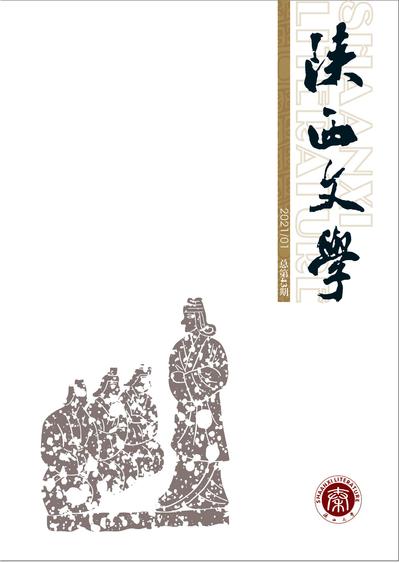
写作的理由
——作者王善常
高考失利后的第一年,我一边在家帮着父母干农活儿,一边写诗。当时我坚信,即使没考上大学,我也完全可以通过文学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还别说,那年我真的就在报刊上发了几首小诗,总共得了三百二十块钱的稿费。稿费虽少,但意义重大,它坚定了我靠文学改变命运的信心。
可第二年我就放弃了,文学虽然美好,但在繁重的劳动和贫困的生活重压下,却根本无力支撑起一个人的一生。我忽然意识到,靠文学改变命运的想法太过幼稚,也太过自私,我必须放弃。这是很痛苦的领悟。领悟之后,我怕自己反悔,立刻把我写的那些诗稿投进了灶坑。望着燃烧的诗稿,我怀着不甘、屈辱和愤怒高声地骂了一句:去你妈的文学!
那之后我就走上了打工之路。在二十多年的打工生涯里,我干过工地的小工、钢筋工、外墻保温和粮库的装卸工。我也慢慢地由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,变成了一个颓废、麻木、丧失了理想的中年人,白天机械地流汗干活儿,晚上喝得酩酊大醉。似乎我的一生已经注定要庸庸碌碌地过下去了,直至死亡的到来。直到2016年的某一天,在一次醉酒之后,我才忽然醒悟,再这样浑浑噩噩、醉生梦死地过下去就太没意思了,我必须振作起来,改变自已,于是我又开始了文学创作。
从2016年至今,我写过不少以农民和农民工为素材的小说。我本身就是个农民,又做过二十几年的农民工,我了解他们。因为了解,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有义务把这些东西写出来。不因为别的,只因为我熟悉,除了写他们以外,我写不出别的东西。
《流星》这篇小说讲了一个发生在工地里的凶杀案。这个故事我是我从工友那听来的。我在写这篇小说时用了一种我以前不曾用过的结构方式,把与这个凶杀案相关的七八个人分成了若干个章节,每个章节都用第一人称来讲述。我的用意就是尽量贴近每一个人,这样会给读者一种代入感。实话实说,我这篇小说只是想借助一个诡异的凶杀案,来向读者展示这些深处底层的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。至于那个杀人的故事,我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载体。毕竟当今社会什么稀奇古怪的事读者都看过,而那些底层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却没有被真正地揭示过。
《劳奴》里的情节许多人都会觉得不那么真实,以为我是完全凭空虚构的。如果你这样认为,那就错了。这样的事真实存在,尤其是在二十多年前,有不少民工都曾遇到过。那时黑社会很猖獗,他们经常骗民工去给他们出苦力,不但不给发工资,而且还限制民工的人身自由,轻则打骂,个别严重的甚至会对民工下毒手。我写这个小说的意图就是告诉读者,在你们看不到的阴暗角落,确实有一群民工,遭受过你们难以置信的苦难经历。但我要声明一下,这篇小说不是在向读者贩卖底层人的苦难。苦难的本身并没有意义,对苦难的思考才有意义。苦难从来也不值得大肆渲染,因为苦难只会得到廉价的同情。我只是在用小说的形式,把那些被遮蔽的现实重新呈现出来,试图改变读者对底层劳动者的一些认知。
不可否认,在这个社会里真的有一个底层存在。去年总理说中国目前还有六亿人的月收入不足一千,这句话让许多人瞠目结舌,甚至难以置信。但这就是事实,这些人的生活,你看或不看,它就在那里,不是你闭上眼睛假装不存在,它就消失了。你不了解只是在你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道隐蔽的隔层。
其实分层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。社会分层是一种有等级的社会结构,通过这种结构,财富、权力和声望在不同社会地位的拥有者之间被不平等地分配,因此社会分层本身体现了社会不平等。
所谓“底层”,是指存在于社会中的一个弱势群体,这个群体十分庞大,包括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,和那些从农民蜕变出来的农民工。他们处于社会阶层的最下面,在经济、文化、组织等方面资源匮乏,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诉求,普遍缺乏话语权。基于这种原因,前些年在文学界涌现出了一大批以底层为题材进行写作的作家,俨然已经成了底层的代言人。但事实上,有很多从事底层文学写作的作家并不是来自于底层,或者已经脱离底层很久,他们底层生活体验匮乏,并不能真正了解底层人民的工作和生活,更别说去揭示底层人民的精神意义和复杂的人性了。他们只能靠想象力和已获得的知识,片面化、机械化、平面化、概念化地写出所谓的底层文学,有一点假惺惺的感觉,缺少细腻强烈的东西。所以说,我们现在面对的只是一个被知识者叙述出来的“底层”,真实的底层仍然处于一种匿名的状态。正因为如此,关于底层的叙说就显得游移不定、闪烁其辞。
时至今日,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学现象,底层写作已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,不仅无所节制的苦难叙事让读者感到了厌烦,而且就连他们称为悲悯的人道情怀,也常因写作者自渎式的创作心理而令人生疑。可以确定的是,一旦作家的真诚与否都成为了问题,那么底层写作引以为傲的为生民请命,也就蜕化成了作家们炫耀苦难的写作游戏。由于过度耽溺于民众的深重苦难,反而削弱了作家表现底层生活的书写力度。
虽然我反对给底层写作贴上标鉴,但我一直坚定地认为,以底层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依然有它存在的理由,只是看作者如何去把握。只要本着揭示真相,引起思考的目的去写,少一些夸张,多一些真诚,这种题材的作品依旧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。还有一点,我认为底层写作不是在向社会反映底层的述求,只是一种揭示,如同推开一扇窗,让读者看到另外一种生活一样。
回顾这几年的写作时光,我内心很不平静,在这几年里,我收获了许多成功的欢乐,当然也付出了许多的艰辛。我所谓的写作,不过是为了在光阴流逝中让自己能够稍感心安,同时也是在对抗我庸庸碌碌的人生。在经历了几年的写作之后,我现在认为,文学真的能够改变命运。我现在所说的改变命运,不是说文学就一定能够给我带来财富和地位的改变,而是说,文学能使我原本庸碌平凡的人生充满希望和幸福。这就是我要说的写作的理由。
——以上节选自《陕西文学》2021年01期
